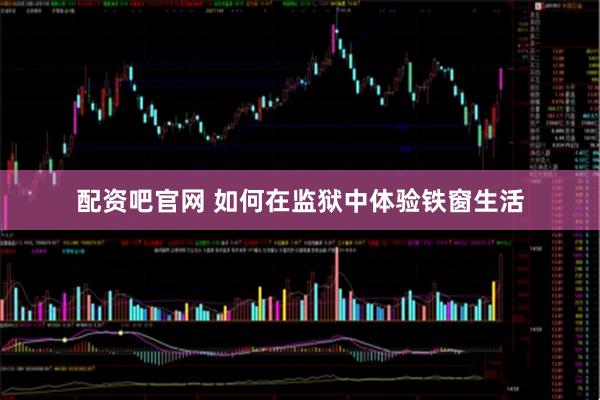
 配资吧官网
配资吧官网


“咔、咔、咔!”监狱的吵闹声中,或许有囚犯用手中的凿子有节奏地敲打碎石,这是他们日常的劳役,也可能是在掩护越狱的同伴——尽管不常发生,但也曾有人成功逃狱。
他们的故事本应随着这些声音一同消散在夜色里。
在1995年,香港政府将域多利监狱、前中区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一同列为古迹,并在香港赛马会的支持下逐步完成活化、保育,最终形成“大馆”这一文化艺术地标,至此,故事也被挖掘、展出,带到公众的面前。

大馆的建筑模型
建筑、历史、悬疑、想象…...香港是一个由神秘空间交错形成的复杂地区,这里从来不乏都市传说与类型命案,人们在具体的空间中构筑起自己对于香港的认知,而那些未曾涉足的空间,则给予了足够的想象留白。
在NOWNESS Paper夏季刊“香港折叠”专题中,我们试图走近这些空间、破除迷雾。这个过程就像拿起一把解剖刀,在切开香港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面后,悬疑的终点指向人们内心深层的共情和恐惧——殖民的管治,逼仄的生活,无根的飘零者。
在生与死、规训与越轨、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,香港浮现出另一面。这是第二篇,大馆的域多利监狱。

策展人钟妙芬在大馆
NOWNESS在5月末前往香港拜访,大馆晴空万里,馆内人来人往,咖啡店和酒吧四处可见,游客们在古老的芒果树下拍照留念。
大馆文物事务主管钟妙芬博士及其策展团队将不同视角的声音、记忆与艺术作品注入古迹,尝试与当下重建联系——当一座监狱变成展馆,我们该如何面对它背后的复杂历史?对钟妙芬而言,历史已经过去,人们需要的不仅是面对,更是理解其复杂性、带着反思迈向未来。

大馆并非单一建筑,而是由多栋建于不同时期、风格各异的建筑组成,这些建筑共同构成了警署、法庭和监狱这一整套权力机器。
整个建筑群坐落在香港的心脏地带,如果从中环地铁站出发,乘坐户外扶手电梯系统便能抵达。一路上,两侧的窗外是高耸入云的写字楼,电梯栏杆挂满了近期文化活动的海报,入口左侧是一座红白相间的英式建筑,眼前的红砖楼却有着中式的瓦顶,透露出这里悠久且复杂的历史。


大馆建筑群
大馆几乎贯穿了香港整个现代史——19世纪40年代,香港开埠初期,这里被英国殖民政府选来兴建监狱和法庭。随着香港的快速发展,人口急剧上升、罪案数量增加,监狱扩张,警署也搬迁至此。
180多年来,这里经历过战争和难民潮,也见证了殖民管治的结束:1997年香港回归,9年后,域多利监狱正式关闭。
作为香港最早的监禁设施,域多利监狱曾经用来关押那些违反法律和秩序的人,包括一些底层华人。受审的人中有贼匪、杀人犯与拐卖人口者,也有街头小贩、醉酒水手、街童与乞丐——犯轻微罪行者通常可选择罚款或监禁,但对于大多数被带到裁判司面前的贫苦大众来说,这种选择只是一种假象,数万人因无力支付罚款而锒铛入狱。

大馆几乎贯穿了香港整个现代史
殖民早期,“种族歧视在司法体系中十分普遍”——法律定义罪名,但审判却是由人来完成。在殖民法治体系中,阶层和种族都在影响刑罚的标准,法庭与监狱也绝非单纯中立的空间,而是以建筑的语言树立权威,固化管治下的不平等。
在英治时期的香港,域多利监狱对市民来说是一个陌生神秘的“禁地”,这不乏权力机构通过空间设计所营造出的氛围。
现在这里已经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。人们走上名为“大馆里(Tai Kwun Lane)”的楼梯,穿过气派的白色营房大楼,左手边便是紧邻的两座红砖监狱A仓和B仓,鞭刑、颈枷、脚镣,乃至绞刑,种种刑罚方式都在B仓再现。
在域多利监狱的常设展览中,受罚犯人的老照片和手铐的复制品被放入玻璃柜、陈列在原始的囚室里。囚室的空间不足5平方米,闷热逼仄,待一会儿就让人汗津津的,据说一间囚室往往要关押很多人。

在市民眼中,域多利监狱曾是个陌生神秘的“禁地”
B仓展馆中,每间囚室都被改为独立的展室,有的放映着纪录片,有的留着囚犯的涂鸦,还有的铁门紧锁,透过铁栏可以窥见高处的一扇小窗,那里透着灰白的光线。
展馆各处都摆放着白底的展牌,其中一个写道:监狱是个充斥哀愁的地方,这里让我们深刻反思罪行,人性恶习与人性尊严。“我们要思考的,是怎么透过这些历史去看现在和未来”,钟妙芬说。

钟妙芬说,自己不会修补砖块,她的工作是通过策展让观众真正走进这段历史,与其建立联系。
曾在海外博物馆从事中国艺术展览的她,将大馆的工作视为一次“诠释历史和联系大众”的实践:不是为了美化历史,也不是控诉过去,而是忠实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城市记忆。
策展团队花费大量心力,采访狱卒、囚犯、牧师及义工,借助纪录片、访谈与投影装置,强调“人”的在场,让他们的真实声音直接触达观众。如今,监狱里的石墙是新粉刷过的,铁栏杆也应该经过多次替换,独特的牛眼窗则是原件,但真正令这个空间动人的,是人们在此留下的痕迹——涂鸦、诗句还有屏幕里低声讲述的他们的故事。


域多利监狱
在B仓的背后,楼梯尽头旁,是另一座监狱D仓。它紧挨着监狱的操场,先后被用作囚室和医疗室,如今这里设有名为“创伤与疗愈”的展览。入口的铁门是灰蓝色的,进入后的走廊墙面是明黄色,在尽头的一间囚室里,粗糙的墙壁上交替投影着许多女性囚犯的绘画。
那些画作有着孩子般笨拙的笔触,满是创口贴的心脏,交叠在一起的有着伤疤的手,还有满纸的水滴,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,它们伴随着温柔的音乐一一出现。一块被塑料板保护起来的涂鸦里写着:“爷爷,奶奶,我好想你啊”。
一位曾在监狱工作过的牧师在放映的纪录片里说:“很多时候,是因为监狱的围墙,让我们不了解里面的世界。我们在外面生活,可能会以为里面的都是坏人,外面的是好人。”这也是钟妙芬觉得非常有启发性的一句话,而且,更重要的是,“其实我们要反思,世界是否真的就这样被一道墙隔开了‘他们’和‘我们’。”


域多利监狱
活化保育后全新的大馆不再只是呈现“囚犯”,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。囚犯入狱是违背了法律,囚禁本身已是一种惩罚,刑期则是在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,而钟妙芬说:“当他们重返社会的时候,社会应该如何给予他们支持,也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。”
基于真实的个体经验的展览,将昔日域多利监狱从权威的身份中抽出,变成了一个倾听被忽视的人的声音的公共空间。它提醒人们面对历史,同时也呼吁着同理心和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支持。更何况,在很多时候,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之间,并没有那么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。

2018年5月,在关闭了近10年后,大馆正式向公众开放——活化工程耗资超过38亿港元,这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、最复杂的文物活化工程之一。
如今,这片占地为13600平方米的古迹,矗立在寸土寸金的中环,蜕变成古迹及文化艺术中心。曾经喧哗的“历史之地”现在充满了咖啡的香气,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,人们在大叶榕和芒果树下闲谈,阳光倒是一如既往的毒辣。
D仓一旁是赛马会艺方,它是国际知名的当代艺术展馆,穿着时尚靓丽的年轻人常常在馆内的旋转楼梯上参观、拍照,一不小心就会闯入他们的镜头中。馆外的监狱操场上展览着波兰艺术家艾莉斯亚·夸德的《等候亭》,六座宛如囚室的玻璃砖结构与多个嵌有巨石的椅子零星排布,整个地方干净整洁,并且安静。

大馆建筑
很难想象大馆曾经是处决囚犯的地方,也很难想象,那曾回荡在整个街区的可怕的哭喊和嘶吼声,以及附近的居民曾如何对这个地方讳莫如深。如城市学者大卫·哈维所言,空间本质上是权力的产物。在城市空间的再利用过程中,始终存在一个根本问题:谁被欢迎进入?谁却无声地被排除?
今天大馆里的,是游客、市民、学生和艺术作品,导览信息详尽、各色文化活动琳琅满目。展览将历史娓娓道来,让许多曾经的囚犯在这里发声;但与此同时,我们也应该意识到,那些未被拍摄、未能进入展厅、死去或者选择沉默的人,他们的过去和记忆,如同从砖墙越狱而出的人,悄然消失在了历史书页中。
砖墙高低不一,砖块各异,曾在不同的时期加固加高,仿佛是被不断修订、补写的历史本身,有些砖块早已风化,如同有些记忆无法被复原追溯。古迹的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人的,钟妙芬在访谈中强调: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和社区共同拥有的资产。”

大馆建筑群示意图
在未来,钟妙芬和她的策展团队正在筹备新的展厅。“时代已经改变了,最重要的是去研究,让这里与社会更紧密地连接起来。”
如今,围墙旁边早已停止加固。大馆有多个出口可以自由离开。外边车水马龙,车辆呼啸而过,红绿灯声音滴滴不停,为视障人士提供便利,它们是这里崭新的声音——声音在分秒中消逝,建筑抵御遗忘的洪流。




NOWNESS Paper 2025夏季刊邀你一起揭秘悬疑档案:为什么要伪造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度?如何跟油麻地的鬼魂一起散步?如果和AI动了真情,要怎么离开这场戏?明知魔术是一种欺骗,观众为什么还要沉溺其中?听,你会如何形容一声枪响?是什么让章子怡嚎啕大哭、浑身颤抖?创造死亡搁浅的小岛秀夫,也会害怕死亡吗?



配多多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